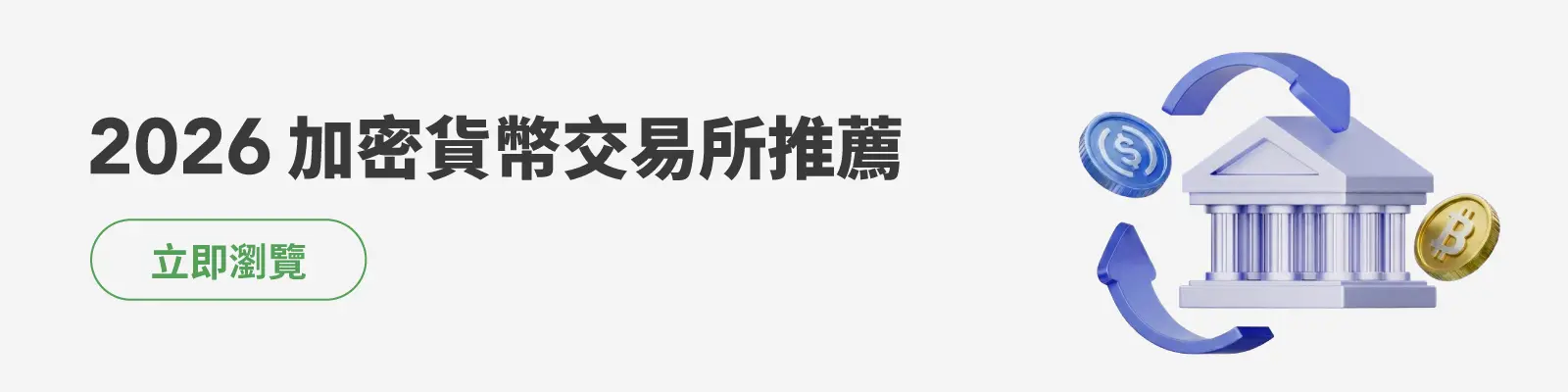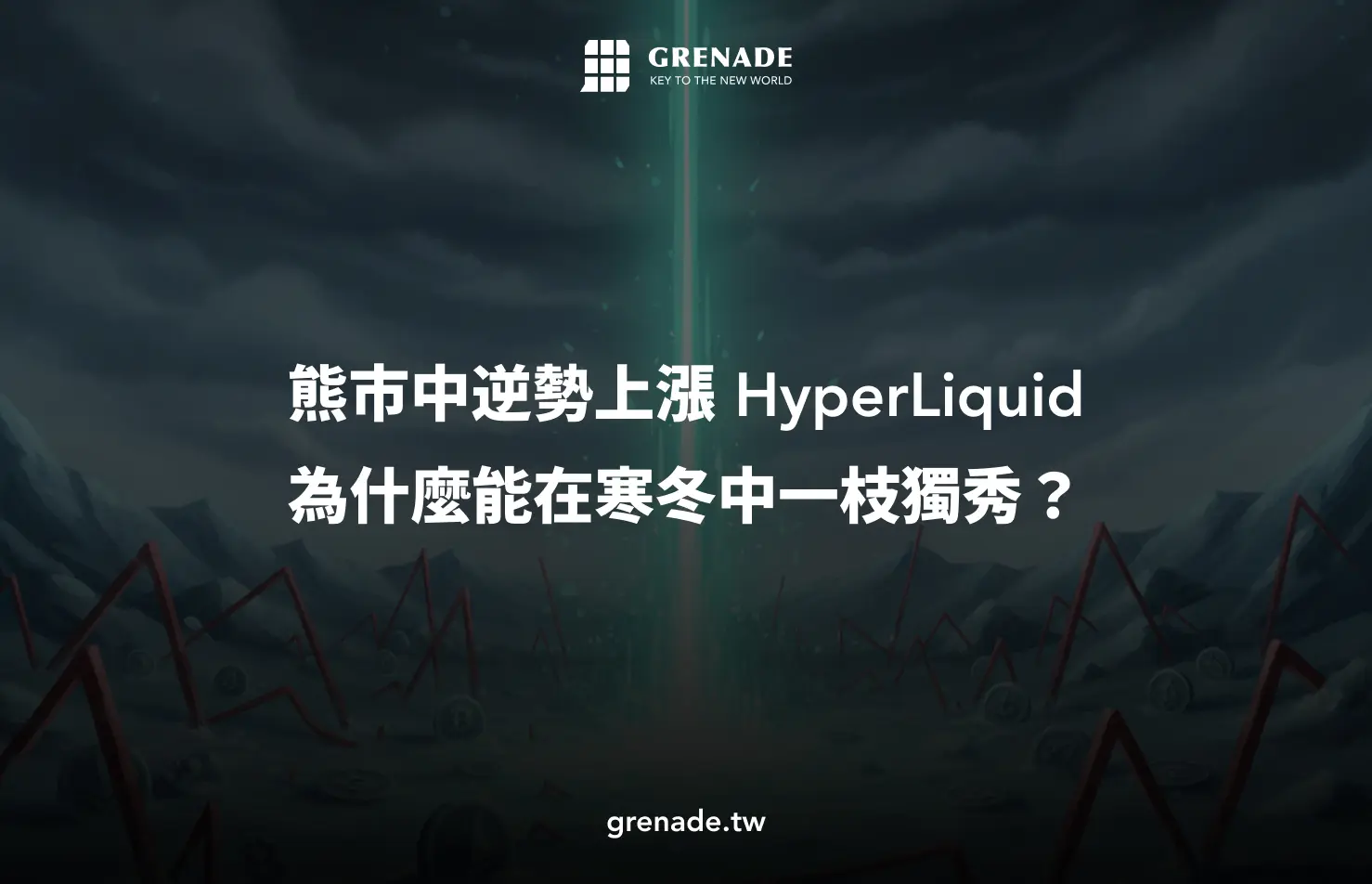比特幣的「中年危機」:元老級 Crypto 如何贏得 Z 世代青睞?
比特幣正面臨一場全新的生存威脅:這並非來自美國、中國政府或超級計算機,而是「世代冷漠」的風險。
比特幣誕生之初,只是個不起眼的「小眾事物」。它既不是矽谷搞出來的創新產物,也不是各國央行開會研究的結果。相反,比特幣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中應運而生,時機恰到好處,且自帶深刻的顛覆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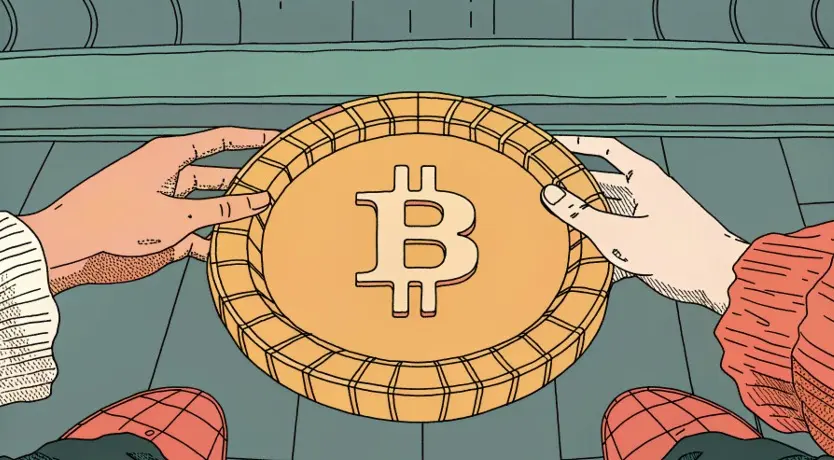
撰文:Christina Comben|編譯:Saoirse,Foresight News
神秘人物中本聰在密碼朋克郵件列表上發布了一份白皮書,提出打造一個點對點支付網絡,這個網絡能夠繞過 2008 年後金融體系中存在漏洞的運作機制。
彼時的比特幣,是「對抗性貨幣」,是直接反抗救助計畫、銀行破產與中央計畫的工具。早期持有者將自己視為「數位叛逆者」,為一種全新的「自由貨幣」搭建基礎設施 —— 它不受審查、無國界限制,也不會被官員的心血來潮或老舊機構的失靈所束縛。 2009 年 1 月 17 日,中本聰曾發文表示:
「或許還是買點比特幣比較好,以防它真的流行起來。如果有足夠多的人都這麼想,那這件事就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。」
從「叛逆先鋒」到「機構寵兒」
15 年間,比特幣從晦澀難懂的技術白皮書,發展成了價值超 2 兆美元的全球貨幣網絡。曾經遙不可及的「監管認可」,終於迎來曙光:起初是監管機構小心翼翼的試探,後來則成了佔據新聞頭條的官方認可。美國財政部長 Scott Bessant 在比特幣誕生週年紀念日時評論道:
「白皮書發布 17 年後,比特幣網路仍在穩定運行,且韌性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。比特幣永遠不會『宕機』。」
從現貨 ETF 上市、華爾街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,到美國政府通過相關法案、上市公司將比特幣納入資產負債表 —— 每一個里程碑事件的達成,都意味著這位「初代叛逆者」似乎征服了一座又一座高峰。
但伴隨著「合法性」而來的,是一個更隱密且緩慢發酵的威脅:「相關性」。能撼動世界的技術,其生命力完全取決於它所承載的「敘事」能否引發共鳴。而年輕一代,顯然對比特幣的敘事不買單。
比特幣的「死亡訃聞」堆成山
為比特幣撰寫「死亡訃聞」,早已成了一種乏味的套路(甚至可以說是一個「產業」)。無論是早期程式碼的模糊性、Mt. Gox 交易所的災難性駭客攻擊、中國的挖礦禁令、監管機構的嚴厲打壓,還是量子運算帶來的潛在威脅,宣稱「比特幣已死」的新聞標題至今已超過 450 個。
「奧馬哈先知」華倫・巴菲特曾稱比特幣是「糞土不如的資產」;摩根大通 CEO Jamie Dimon 則嘲諷道:
「我一直完全反對加密貨幣、比特幣這類東西。它們唯一的真實用途,就是給罪犯、販毒者…… 洗錢、逃稅提供便利。如果我是政府,我會直接取締它。」
然而,每一次危機似乎都在強化比特幣的「免疫力」。無論遭遇監管恐慌、安全事故,或是熊市寒冬,比特幣網路總是能持續運轉,區塊不斷生成,一種新的敘事也隨之誕生:比特幣是「不可阻擋的」。
這種信念已經滲透到各個層面,就連俄羅斯總統普丁也曾公開表示:
「比特幣,誰能禁止它?沒人能做到。誰能禁止其他電子支付工具的使用?同樣沒人能做到 —— 因為這些都是全新的技術。」
事實上,對數位時代的千禧世代而言,比特幣早已成了黃金的「精神繼承者」:它抗壓性強,而且(若「存活」也算是一種優勢的話)幾乎可以說是「不朽」的。
但正如加密貨幣安全公司 Casa 的首席安全官、比特幣安全專家 Jameson Lopp 先前對 CryptoSlate 所說:比特幣面臨的最大威脅,並非技術突破或監管博弈。到了 2025 年,真正的威脅是「冷漠」—— 願意關注它的年輕人太少了。
Z 世代:沒錢,也沒比特幣
「Z 世代」(Zoomers)是伴隨著 iPhone 和 Instagram 出生、看著 YouTube 和 TikTok 長大的一代。他們在「晚期資本主義」的疲憊氛圍中步入成年,正在改寫經濟規則。
普通 Z 世代畢業生面臨薪資停滯、買房無望、入門級崗位消失、信用卡債務飆升的困境。當「未來」的邊界只到下一筆薪水,又何必為明天儲存價值?正如 InvestiFi 數位資產副總裁 Sean Ristau 對 CryptoSlate 所說:
「比特幣最初是對金融體系的直接挑戰,是一種抗議形式。現在它卻更像『數位黃金』,主要被巨頭和銀行掌控。對那些要應對通膨、債務和生活成本上漲的年輕人來說,這樣的形像根本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。」
無論比特幣在市場上顯得多麼「強勢」,在許多 Z 世代眼中,它都帶著一股可疑的「嬰兒潮世代的味道」。比特幣最早的支持者們身上帶著 2008 年金融危機的「戰鬥傷痕」,而 Z 世代熟悉的,只有 Meme 股票、Robinhood 選擇權交易和狗狗幣這類代幣。
ProCap BTC 資訊長、Bitwise 顧問 Jeff Park 警告稱,比特幣的敘事必須改變。他認為,Z 世代追求的是「意義」,而非抗通膨工具:
「說到底,如果年輕人不接受比特幣,那整個比特幣的邏輯都會崩塌。」
在最近一期《比特幣的故事》播客中,加密貨幣倡導者 American HODL 也承認:
「Z 世代對比特幣興趣不足,這其實是個大問題 —— 因為他們太『虛無主義』了。我們必須持續主動接觸他們,試著喚醒他們,告訴他們:『兄弟,為了自保,也為了你自己好,趁現在還來得及,趕緊行動起來!』這兩方面原因都很重要。」
政治背景:紅黨與藍黨的「比特幣持有戰」
圍繞比特幣的黨派分歧,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尖銳。當拜登政府加大「扼制行動 2.0」(Choke Point 2.0)對加密貨幣企業的壓制時,民主黨給出的立場成了「加密貨幣有害,監管必不可少」。
與之相反,MAGA 陣營的共和黨人、自由意志主義中堅力量,以及部分溫和的中間派,如今將支持比特幣視為「彰顯財政獨立與國家復興立場」的方式。
(註:MAGA,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」(讓美國再次偉大) 的英文縮寫,最初是美國前總統唐納德・川普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提出的核心口號,後來成為其支持者群體、相關政治運動及保守派陣營的標誌性理念符號。)
但 Z 世代對此完全不感興趣。他們湧向那些「團結高於投機」的線上社群。比特幣的政治敘事,原本是「擺脫政府控制的自由」,如今卻要對抗日益加劇的經濟焦慮 —— 以及人們對美國政府,乃至所有機構的普遍不信任。 Park 警告:
「左派候選人在選舉中不支持比特幣,是有原因的 —— 不是因為他們害怕『體制』,而是因為他們認定支持比特幣會損害自己的利益。這絕對是件壞事。比特幣要想成功,就必須成為『比特幣與曼達尼(左派政客)』的共同平台,而不是「比特幣與阿克曼(右派資本家)」的專屬工具」的專屬工具。
當川普和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將比特幣吹捧為「愛國技術」時,傾向左翼的 Z 世代卻轉向了佐蘭・曼達尼這類社會主義領袖。在他們眼中,比特幣成了「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副業」(甚至更糟),是「守舊勢力」的一部分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,它早已不是那個懂街頭文化的「叛逆者」了。
為何比特幣的概念無法打動年輕人?
比特幣最初的核心主張 ——「擺脫銀行控制、抗通膨儲蓄、數位資產不可沒收」—— 在年輕人中根本激不起多少熱情。對他們來說,金錢不像是「需要守護的堡壘」,更像是「無限遊戲裡的積分」:永遠在流轉,永遠在變動。正如 Bitget 錢包首席行銷長 Jamie Elkaleh 對 CryptoSlate 所說:
「Z 世代的投資文化節奏更快、更社交化,也更依賴 Meme 傳播。他們更傾向於社群驅動代幣、AI 關聯資產和創作者經濟 —— 因為這些東西能讓他們感受到『參與感』,也符合他們的數位行為習慣。
年輕用戶往往將比特幣視為『基金和財庫的資產』,而非『自己能直接參與的平台』… 比特幣『數位黃金』的敘事雖然能帶來安全感和榮譽感,卻缺乏『互動性』和『目標驅動的活力』—— 而這兩點,正是這一代人參與金融活動的核心訴求。 」
Ristau 補充道:
「加密貨幣持有率正在快速上升(超過一半的 Z 世代曾經持有過數位資產),但比特幣的受眾仍然偏向年長、富有群體,且以男性為主。年輕用戶追逐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:有明確目標的 Meme 幣、AI 關聯代幣,以及有趣、實用或由社區驅動的社交或遊戲類項目。那麼,問題到底出在哪?」
是「人口結構問題」,還是「人口結構機會」?
25 歲以下的年輕人對世界和自身處境越來越失望,這有什麼奇怪的嗎?高通膨、財富累積管道堵塞、對父母那代人依賴的機構完全不信任 —— 這些都是他們面臨的現實。
矛盾的是,這種困境或許能催生比特幣的下一波採用潮。 Cardone Capital 執行長 Grant Cardone 對 CryptoSlate 表示:
「比特幣根本不存在『青年困境』。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持有者的年齡,而在於心態。有人告訴 Z 世代『要炒 Meme 幣,不要累積財富』,於是他們就去追逐快錢,而非能傳承的長期資產。比特幣是為『有長遠眼光的人』設計的 ——」人明白,『控制權、稀缺性、自由』財富的基礎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,比特幣所謂的「人口結構問題」,更像是「人口結構機會」。由「渴望獲得數位所有權的世代」所引領的新潮流,或許即將到來。正如 Elkaleh 所強調的:
「比特幣的『青年困境』,根源在於其『機構成熟度』與『文化相關性』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。年輕投資者的持有意願並未消失,但他們接觸加密貨幣的『第一個觸點』,越來越多是『與文化相關的資產』,而非比特幣。雖然機構和 ETF 增強了比特幣的可信度,但也讓它偏離了「人類」社區的重」。
彌合鴻溝:比特幣如何融入青年文化?
那麼,比特幣該如何突破「年長投資者主導」的現狀,吸引 Z 世代中的創作者、遊戲玩家和數位創業家?答案在於「實用性、信任與文化融合」。 Cardone 的觀點直截了當:
「比特幣不需要為 Z 世代『改變自己』;而是 Z 世代需要『清醒地認識比特幣』。但我可以告訴你,要讓比特幣更有吸引力,有三件事必須做:教育、賦能與體驗。」
Ristau 認為,重點應更多放在「比特幣的實用性」和「全球範圍內不斷增長的應用場景」。他指出:
「抗通膨、金融自由、降低全球匯款成本 —— 這些都是關鍵賣點。近年來,加密貨幣匯款量增長了 400% 以上。這個故事才應該是宣傳的核心。」
Elkaleh 也強調,比特幣的敘事需要「煥新」,而且必須牢牢紮根於「實用性」:
「同樣重要的是更新敘事框架。『數位黃金』的定位能引起機構和長期投資者的共鳴,但無法解釋比特幣對普通人的『實用價值』。對年輕用戶來說,比特幣的『相關性』體現在它能『實現什麼』—— 隱私保護、自我託管、抗審查、支持公益導向的交易。」將這些核心原則與跨國資金相似」—— 隱私權保護、自我託管、抗審查、支持公益導向的交易。將這些核心原則與跨國匯現’。
比特幣經歷的生存威脅,比任何數位產物都多。它熬過了華爾街巨頭的唱衰,也頂住了監管機構的壓力。但它面臨的最大威脅,或許是「失去青春的火花」── 那些賦予比特幣靈魂的叛逆者、夢想家和建造者。
比特幣最終會成為「博物館裡的展品」,還是「改變世界的貨幣」?答案一如既往,取決於「有多少人願意接過它的火炬」。
歸根究底,「自由貨幣」的存續,取決於能否將敘事從「傳承資產」轉向「有意義的故事」。比特幣從誕生之初就不該是「乏味的」。要在未來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裡持續發展,它需要的是「生命力」,而非僅僅是「價值」。
新手閱讀:《 比特幣 ETF 台灣投資者怎麼買? 》